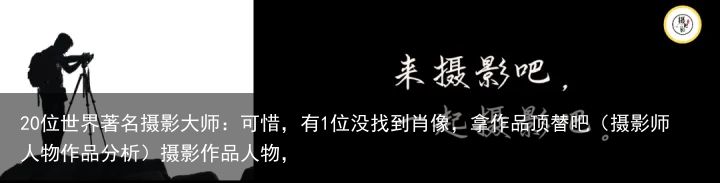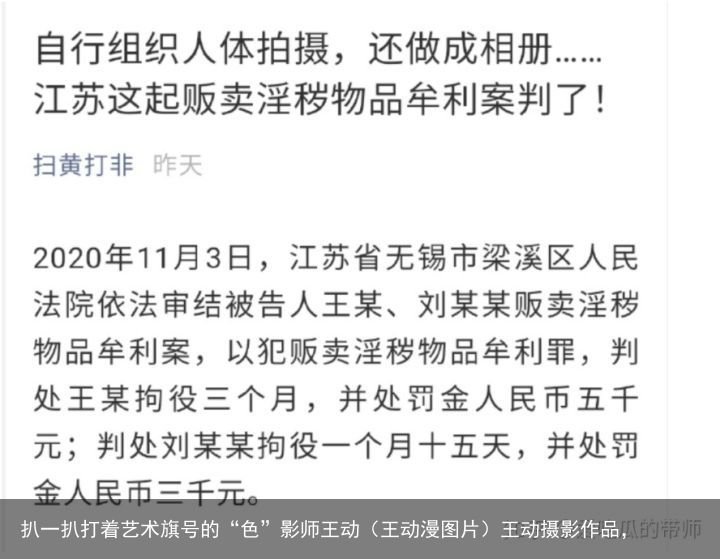诗人的摄影:眼前摄影心底诗(摄影作品阐述)摄影作品描述,
翟永明 《触碰》 摄影
翟永明 《建筑》 摄影
◎剀弟
展览:全沉浸□□脚本(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
时间:2022.11.25-2023.1.3
地点:厦门市集美区市民广场展览馆
真正的诗人,不局限于任何一种媒介。
在厦门市集美区市民广场展览馆里,沿着第八届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的展览参观,很快能看见一个空间里寂静地开出摄影与文字的花。“无界影像”板块继去年诗人北岛的摄影展之后,今年又邀请到了另一位诗人——翟永明的摄影作品,同样由沈祎策展。诗歌与文字互相映照,将硕大展馆里这一小块空间变成独立的弥漫着快感和痛感的空间。
“地球将死于何种形态?
人类末日?那必将是一种凄楚的壮丽
我愿登上某个山头 如果
能将世界收于眼底
我愿以一个亲历者而非预言者
扑向最后的神秘”
——翟永明《全沉浸末日脚本》
“全沉浸□□脚本”,当我们看到这个展览名字的时候,对其中隐去的两个字和这种用方框隐去的方式非常好奇。其实熟悉翟永明诗歌的朋友和现场的观众会看到这一句的本来完整版本——“全沉浸末日脚本”,这也是翟永明在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诗集的名字,这本诗集是翟永明在疫情后的几年里生活感悟的鲜活反应。在现场我们也能读到这一首同名诗歌。在诗中,诗人是预言者,更是一个穿越时空的见证者:“人类的毁灭方式有几种?我们的走向包含了希望吗?除非你问:接下来呢?”
翟永明的身份除了诗人,也是艺术和文学评论者、散文作家、文艺活动组织者等。她的摄影创作实践开始得比较早,并且有意识地尝试观念摄影和摄影拼贴创作,比如她将朋友和自己装扮成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罗的形象进行的摄影和自拍,以及参照《韩熙载夜宴图》的形式创作的摄影长卷《亲密的人中间》,都在这次展览中有所呈现。
对于诗人来说,摄影和写作一样,是抵抗涣散的方式。“在这个越来越快、越来越具不确定性的时代,很多东西难以把握。我喜欢独自创作的工作:写作、摄影是我与自己独处、与自己对话的方式,是能够只靠自己来掌控的少数事情,我靠它们给我提供能量和抵抗负面情绪。”
《全沉浸末日脚本》里的“末日”是诗人翟永明对这个不确定时代的一种感受。但是诗人并没有沉湎于任何的负面情绪,也并不把末日当成末日来描写,而是跳出来质问永生,不断地用摄影和写作实践做出反应——她写战争、写疫情,写所看的美剧《西部世界》,相机不停,笔耕不辍。
在灰色的背景墙下,翟永明的摄影——大部分是黑白——被打印成像大号明信片一般大小,一张张贴在墙上,间或装裱在由黑色卡纸衬托下的银色细边框里,像是一个个断句符号。这些摄影作品沿着墙面,挂在普通人心脏的高度,一路编排下去。观众边走边看,如同读一首错落的诗歌。
它们并没有如一般看到的摄影作品被标注上拍摄日期、并加上系列标题呈现,而是集合了多年及最新拍摄的照片,被策展人根据展览的逻辑打碎重组,每一组作品旁边有截取的诗句片段,诗歌和摄影就这样无缝转换。
这些我们看到的图像非常微妙:它们尺幅不大但包含细节和力度,明显带有诗人的气质和痕迹,有一种女性纤细敏感的气势。而间或穿插的诗歌让这些图像飘浮在不确定的时空里,诗人的文字不锚定于任何一个过去的时空,带有一种未来感,正如这些图像中有不少拍摄的是我们熟悉的景观和事物,却去掉了它们原本的背景——
古建筑中带花纹的窗户、由砖砌成的墙面纹路、游泳池水波下的网格,这几幅自成一个短句。植物的抽象纹理、反光里的自拍像、艺术家马修·巴尼的铜镀画刻纹,它们组成了一段诗。
影像可以成诗,诗歌也可以与图像产生有趣的互文,这是来自策展人体悟到的通感。食物罐头的图像旁边的诗句里包含着“爱人必被爱吃”,铁栅栏网格的图像旁讨论着“伤害是一种体温”……这样的联想有时候可以是直接的,比如有关植物的摄影旁边的诗句可能也与植物有关;有时候则有点跳跃,比如一卷碎碎珠帘或者光斑也许可以关联到星星点点的宇宙之歌。但是无论诗人还是策展人,都强调摄影并不是诗歌的图解。毋宁说,真正的诗人,不局限于任何一种媒介。好诗人都会摄影,因为好的文字自然具有画面的通感。
对于符号隐喻的敏感也是诗人摄影的共通点。翟永明的摄影作品里出现了不少的几何图形和花纹。除了具有的抽象美感之外,它们似乎也有一些自我的映射,窗户与门具有一种开放与遮蔽、内与外的联想;模仿自然的建筑曲线形态、弗里达的标志性装束,有意地勾连起历史和自然中的生命力和活力。
诗人这样描述自己摄影和诗歌的相同点:“这次参加摄影节的作品,和诗歌有相像的地方,它们都是抽象的、弥漫性和发散性的。它们也许能够反映出我的某些偏好、我对某些事物格外的关注,以及我所认为的周遭事物皆充满诗意的态度。这些图像大多数是我在生活日常中随手拍摄的,是一些偶然的发现和瞬间的捕捉,带有强烈的个人视点。它们并没有提供任何的具体意象和主题,而是敞开思路让观者去想象和二次创作。”
翟永明也喜欢在旅途中拍照,她常会去一些文学作者的故居,寻找故居里的镜子,并在镜子前留下自己的影像。与其说这是游客的自拍照,诗人的自拍似乎更想寻找一种与空间和空间里的幽灵的对话,留下的模糊或者变形的面孔成为一次次自我存在的确认、一次次在时空中的幽游。在展览现场,策展人也在入口处放置了一个波浪形的竖镜,在展览结尾的墙面贴了三面小镜子,映衬着空间。我们在镜面中观察自己,也与诗人的作品进行了某种对话。
这个时候我们明白策展人将“末日”隐去的含义,这是因为每个观众会有自己的感受,也都有权利谱写自己的剧本。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信息被隐去,但是隐去并不等于没有发生过。每个人对末日的定义和看法也并不相同。面对时代和人类的命运,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无力,但是借着对这个标题的改写,策展人说:“记录我们的内心并不是诗人或者艺术家的特有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有意识去书写属于自己的剧本,去记录自己的声音,填写这框里留白的部分。”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